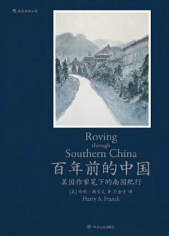 【书 名】百年前的中国: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
【书 名】百年前的中国:美国作家笔下的南国纪行
【作 者】(美)哈利·弗兰克(Harry A. Franck) 著 符金宇,后浪 译
【出版者】四川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I712.65/5584
【阅览室】社科一阅览室
作者简介
哈利•弗兰克(Harry A. Franck)被誉为“流浪王子”,是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游记作家之一,一生共完成三十余部作品,能熟练使用英、法、德等多国语言,以作品Zone Policeman 88,成为1913年全美最畅销作家。
符金宇,男,1978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广东省翻译协会理事,出版译著《美国军队及其战争》《最后的战役》《基辛格的影子》,专著《日本足球史》。
内容简介
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初来到中国游历,反对同胞们沉迷于租界中享乐的生活态度,利用基础的交通工具和徒步,深入中国广阔的南方地区,足迹遍布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的乡村市镇,广泛接触中国社会的各类人群:军阀、进步学生、租界买办、贫苦乡民、传教士、手工业者,等等。用文字和相机记录下1924年中国南方地区的市井生活细节,总体来说,是非常真实的社会画卷。
序言
马可·波罗的游记虽然举世闻名,有时却不免令人失望。他在游记中,将我们称为“中国”的这个国家,分成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国度,北边被称为“契丹”(Cathay),南边的叫作“蛮夷”(Manji)。虽然近代中国并没有梅森 - 迪克森线这样具体的南北分界线,但这个国家的南北两部分却截然不同,二者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中间地带逐渐过渡。外国人习惯将长江视为分界线,中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政治倾向,但除非再划出一块区域来,称为华中地区——就像不少人实际做的那样——长江流域与南方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多过北方。南行的旅者在穿越北纬34度时会留意到某些突如其来的变化:骆驼、毛驴、北京的马车,还有寸草不生、树木稀疏、尘土漫天的那副北方风光忽然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水牛、轿子,以及狭窄的石板路在一望无际的水稻田中曲折蜿蜒,这块土地纵使谈不上更为干净,至少多了不少绿意。这里水道纵横,可除了嘎吱作响的独轮车之外,极少看见带轮子的车辆;成群结队的劳工挑着担子,二者相映成趣,随处可见。真正的分界线在于这里不再种植高粱、小麦与黍,转而出现了稻谷文化,虽然河南与陕西差不多算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南方绝大多数地区被纳入中华版图也不过千余年历史,但较之两地的人而言,南北差异更多源自彼此对主要农作物需求的不同。
本书主要记录的是我在马可·波罗笔下的“南蛮之地”漫无目的的旅行,而其姊妹篇讲述的则是在“契丹”的故事。正如这本简单的游记所描述的,我只不过四下走走,看看兴趣所至的地方。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向来无意专注于科学研究,也无私心可图;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连一个流浪汉都得展示出自己存在的缘由,那么我也打算尽可能把这一切完整地带回家乡,聊以慰藉那些和我拥有同样普通品味的人。这本书或许描述得过于具体,但至少应该能为某些人提供一剂解药,让他们莫要过多沉迷于与今日中国有关的时事报道,让读者意识到,虽然对于记者来说,只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变或是一次谋杀才算得上“新闻”,但事物的本来面貌往往在于宁静而平淡的日常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在此之前已经持续了数月、数年,并将在今后的很多年里继续下去。
那些智者哲人毫无疑问会觉得接下来的篇章烦琐无趣,不少文字在他们眼中想必定然无足轻重、微不足道。这些人应当去读超现代派的鸿篇巨制,写那些书的年轻一代号称才华出众,对于今日的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只需安坐家中,畅饮私酿,便可为我们指点迷津。我一介老朽,把全副精力都放在这些微不足道的旁枝末节之上,兴许早已错过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我倒是在华盛顿的某家旅馆里见过一位侍者,远比参议员更关心他的门为谁而留。
某些挑剔的读者恐怕会指责我过于现实,这样的指责以前也曾有过,但我更关注的是记录一份平凡的事实,而非炮制“文学名著”。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已有太多的真相被曲解,我们之所以会对中国产生如此错位的印象,部分原因在于有些人心怀善意,极力将其刻画成一个平和完美的社会,借以反衬出我们自身的文明在各个方面的野蛮无序;另一方面则要归咎于“畅销书”的浅薄与无聊,为了引发同情,不惜捏造耸人听闻的情节。正是在上述两类人代代相传的不求甚解之中,创造出今日世人对于中国的看法,而与真相有关的中间地带则远未得到开发。虽然直言不讳或者视而不见会让画面看上去更加诱人,可我总是对芸芸众生的生活更感兴趣,而不是强调污秽不洁的环境、此起彼伏的喧嚣、有时令人难以忍受的酷热以及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无论这些是让人感到不快还是愉悦,毕竟这些现象存在于每个国家,仅凭这些提供的只能是一份虚假的报告。
任何要想走遍中国南方的人,必定都有一条错综复杂的路线。为了让行文更加清晰,我并未完全按照旅程的先后进行记叙;这样做除了让季节时断时续之外并无其他不妥。我在远东的游历不仅包括整个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还包括日本帝国的全部领土与法属印度支那的五个地区,而那些地方又是另一番故事了。本书讲述的是我在一年多时间里几乎毫不间断的旅行经历。如果你觉得我走过的地方看上去并不辽阔,那是因为没有其他地区的交通运输比中国南方要更缓慢。国内的某些朋友以为我带着家人去了中国,想必生活平静安稳。事实上,当我们在回国途中整理记录时才发现我们离开美国其实已有 928 天,在此期间我有整整 435 天没有与家人在一起。
凡身处一国,若想见识当地人的真实生活,必得去往游人不常去之地,还得至少学会几句当地的语言,才能让这一切变得更有意义。考虑到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处境,这一点更是准确。我们这帮身在通商口岸的洋人,在某种程度上受人鄙视、甚至有时遭人憎恨,无疑都应该归咎于我们自己而非中国人犯下的丑行。在通商口岸,像我们这样的洋人为数不少,其中十有八九从未踏出过这块土地。然而,这个国家的人却在整体上千差万别,尤其是在对待“外来蛮夷”的态度上更是如此。大多数中国人对我们充满敌意,或者说至少并不友好,这种态度与他们的内在礼仪相去甚远;而中国人对我们日益熟悉,所以要对这个天朝上国做出真正评价,我们就必须去那些洋人涉足不多的地方。这样的深入旅行时常会让人感觉单调乏味。然而,虽然北起东北、南抵云南的中国人看似差别不大,事实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同。即便两地相距不远,可纵使穷尽一生游历,耗尽柯达公司生产的所有胶片,也无法将这些地域的区别完完整整地道个明白。在中国,如果不是每一个中国人,至少几乎每一寸土地也会向怀有闲情逸致的旅行者展示新的一面;不过令人奇怪的却是另一方面,这里的芸芸众生又犹如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铁块一般,千人一面。这片古老土地之所以如此值得深度探索,原因之一就在于各地习俗或许大同小异,但手工的劳作方式、快捷便利运输手段的缺乏、传统保守的孔孟之道以及每个中国家庭总是希望安居一处的愿望掺杂在一起,使得生活的细节千差万别。这一点与我们的国家形成鲜明反差。西方早已实现大规模生产,广告铺天盖地、席卷全国,一切都是完全一样的标准化。每每走在一模一样的街道上,经过同样风格的商铺门庭,躲避着同一个牌子的汽车,人们非得想破脑袋才会弄清,自己究竟是在波特兰、缅因还是圣迭戈。
在我身处中国的两年里,社会局势混乱不堪,政府统治形同虚设,违法之事层出不穷,兵灾匪祸猖獗之极。许多人喜欢用一本正经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这种人每个国家都有,他们会避开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度,不敢涉足其中。毋庸置疑,这个国家的确危机重重。在某种程度上,暴力威胁着身处中国内地的全体外国人的共同安全。然而,即便身在美国国内,人们也不会因为街头存在不容小觑的危险而选择将自己关在家中,闭门不出。我造访了中国的全部十八个行省,其中绝大多数都已游历殆遍,除了跟随身边的中国仆人,常常孤身一人在外数周。我从未去过的省会城市只有一个,那样做也只是出于个人选择。只要是我的兴趣所在,便从未改变过行程安排,或者回避某条旅行线路,也从未出过哪怕一丁点儿的疏忽纰漏。之所以如此,恐怕在于我在这个昔日的天朝帝国从未感受到真正的生命威胁。去年在母亲陪伴下,我的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游历了中国十八个行省中的九个,在不少动荡的城市里,就住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白天晚上随意徜徉在街头却从未受到蓄意侵扰。每每进一步回想起这些,我必须承认,中国的生活整体上至少对于我们这些西方人来说,并不比在其他西方国家危险。诚然,这些话也不能完全算作事实。过去几年,有些人单凭几条关于中国的头条新闻便会激动万分,大发议论,我的话与他们的看法比起来,也不见得真实多少。因为中国的确存在诸多动荡不安,像我这般鲁莽的人之所以走遍穷乡僻壤却从未遇见,唯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我的运气实在糟糕透顶,总是让我即便身处正确的地点,赶上正确的时间也无法体会到冒险的趣味,而那些远不希望感受这番情趣的人们,却往往得到了比他们本应得到的多得多的乐趣。此外唯一可能成立的结论让我实在难以启齿、羞于承认——毫无疑问,我不止一次碰上过成群结队的不法之徒,之所以从未遭遇骚扰,原因和我这么多年浪迹于其他是非之地却未曾遭受类似骚扰大同小异,仅仅是因为我看起来从来就不像个有钱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