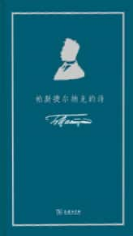 【书 名】帕斯捷尔纳克的诗
【书 名】帕斯捷尔纳克的诗
【作 者】(俄)帕斯捷尔纳克 著
【出版者】中国戏剧出版社
【索书号】I512.25/4645
【阅览室】社科一阅览室
作者简介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20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作家之一,他历经白银时代、十月革命和苏联“解冻”,早年即以其深沉含蓄、隐喻鲜明的诗风蜚声诗坛,1958年以“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生活——我的姐妹》、自传体随笔《安全保护证》和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俄罗斯普希金之家北京分部主任,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委,鲁迅文学奖评委,《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译林》《俄罗斯文艺》《外文研究》等杂志编委,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学者,译有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布罗茨基、佩列文等人的作品,是俄罗斯利哈乔夫院士奖、“阅读俄罗斯”翻译大奖、“莱蒙托夫奖”、俄联邦友谊勋章获得者。
内容简介
《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汇集俄国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各个时期诗歌佳作50首,由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刘文飞教授遴选、译介。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与其复杂艰辛的人生历程相对应,他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界点上,以艺术家的心灵感知这一切。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我们与诗人一起经历由混沌到明澈、由繁复到简白、由嘈杂到和谐的过程,于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于非自由中见证自由。
译序
帕斯捷尔纳克似乎生来就注定会成为一位诗人。
1890年2月10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出生在莫斯科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著名画家,他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所画的插图十分著名,他做过莫斯科绘画、雕塑和建筑学院的教授;母亲罗莎莉娅•考夫曼是一位钢琴家,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帕斯捷尔纳克家经常高朋满座,列维坦、斯克里亚宾等都是这家的常客,未来的诗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浓郁的家庭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青年时期的帕斯捷尔纳克曾跟著名音乐家斯克里亚宾学习作曲,后借口听力不好放弃;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不久,又赴德国马堡大学研习哲学,试图揭开生活的秘密,在得到著名哲学家科恩教授的高度肯定之后,他却突然决定回国:“别了,哲学!”因为他已经感觉到诗歌或许更易于用来破解生活之谜。不过,青少年时代学习音乐和哲学的背景,却无疑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为帕斯捷尔纳克之后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
帕斯捷尔纳克爱上诗歌并开始写作诗歌的年代,恰逢俄国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诗歌时代。他比以象征派诗人为主体的白银时代第一批诗人要年幼一些,却几乎是白银时代诗人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他最初接近的是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领的未来派,可他却和茨维塔耶娃一样,是白银时代极为罕见的独立于诗歌流派之外的大诗人。更为重要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呈现出对白银时代各种诗歌流派的开放性,他的诗中有象征派诗歌的音乐性,也有阿克梅派诗歌的造型感;有未来派诗歌的语言实验,也有新农民诗歌对自然的亲近,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似乎是白银时代诗歌经验的集大成者,就这一意义而言,帕斯捷尔纳克是真正意义上的俄国白银时代的诗歌之子。
在世界范围内,提起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普通读者最先想到的可能还是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因为这部小说已被译成世界上数十种语言,因为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好莱坞影片,因为这部小说引起了一场加剧东西方冷战的国际事件,很多人都认为,正是《日瓦戈医生》使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殊不知,当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因为在当代抒情诗歌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伟大俄国散文传统的继承。”也就是说,主要的奖掖对象还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创作。
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若干中短篇小说、两部自传、四部长诗和十余部译作,但他创作中数量最多的还是抒情诗集,有九部之多。这些诗集像一道珠串,把帕斯捷尔纳克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诗歌创作连接为一个整体;它们又像九个色块,共同组合出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斑斓图画。
1913年,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在刊物上零星发表抒情诗,次年推出第一部诗集《云中的双子星》,尽管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对这部处女作不太满意,评论家也认为这部诗集非成熟之作,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后来曾多次修改其中的诗作,这反过来表明了诗人对自己最早一批抒情诗作的眷念和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这第一批诗作其实奠定了他的诗风,将这部诗集中的诗作与他后来的诗作相比,似乎也看不出过于醒目的差异,相反,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二月》后来几乎成了帕斯捷尔纳克任何一部诗歌合集的开篇之作。1917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第二部诗集《超越街垒》,其中的许多诗作其实引自其第一部诗作,但这部诗作的书名却不胫而走,不仅是关于当时时代的一种形象概括,同时也构成帕斯捷尔纳克人生态度的一种隐喻。当然,让帕斯捷尔纳克赢得广泛诗名的,还是他的第三部诗集《生活是我的姐妹》(1922)。诗集中的诗写于俄国的历史动荡时期,却令人惊奇地充满宁静和欢欣,对叶莲娜•维诺格拉德的爱恋,与俄国大自然的亲近,使得诗人在残酷的年代唱出了一曲生活的赞歌。在诗集《主题与变奏》(1923)之后,帕斯捷尔纳克一度转向历史题材的长诗和散文写作,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相继出版两部诗集《历年诗选》(1931)和《再生》(1932),后者的题目曾被当时的诗歌评论家解读为诗人对其所处“巨变”时代的诗歌呼应,但其写作动机实为帕斯捷尔纳克对济娜伊达•涅高兹的热恋以及格鲁吉亚主题在诗人创作中的渗透,“再生”当然也暗示诗人的返回诗歌。1943年,帕斯捷尔纳克出版诗集《早班列车上》,这部在二战正酣时面世的诗集与《生活是我的姐妹》一样,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世界中的安详与宁静与外部世界中的动荡和震撼构成了独特的对比。战后十年,帕斯捷尔纳克将主要精力用于写作小说《日瓦戈医生》,但这毕竟是一部诗人写作的诗性小说,帕斯捷尔纳克用假托为小说主人公日瓦戈所作的25首诗构成小说的最后一章,所谓《日瓦戈的诗》也应该被视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部独特诗集。20世纪50年代末,帕斯捷尔纳克因为“诺贝尔奖事件”在苏联国内遭到批判,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人们曾经以为,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情绪低落,不久便郁郁而终。然后,帕斯捷尔纳克的最后一部诗集《天放晴时》(1956—1959)却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帕斯捷尔纳克,或曰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更真实的心境,在与伊文斯卡娅的夕阳恋中,在与以佩列捷尔金诺为代表的俄罗斯大自然的共处中,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向死而生的欣悦和释然,这部诗集也因而成为帕斯捷尔纳克整个抒情诗创作、整个文学创作乃至整个人生的一个完美总结。
帕斯捷尔纳克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诗人之一,其抒情诗创作的价值或曰意义,我们或许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首先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别具一格的隐喻系统。帕斯捷尔纳克的诗素以“难懂”著称,在中国也曾被视为“朦胧诗”,这主要因为,他的诗大多具有奇特的隐喻、多义的意象和复杂的语法。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中,复杂的句法和满载的意义与抒情主人公情绪的明澈和抒情诗主题的单纯往往构成强烈对比,而这两者间的串联者就是无处不在的隐喻。与大多数善用隐喻的诗人不同,帕斯捷尔纳克的隐喻不是单独的,而是组合的、叠加的、贯穿的、不断推进的,与此相适应,帕斯捷尔纳克的隐喻往往不单单是一个词,或一句诗,而是一段诗,甚至整首诗,在俄语诗歌中,同样具有此种风格的只有茨维塔耶娃和曼德施塔姆,或许还有后来的布罗茨基。这些组合隐喻会演变成一个个意象,扩大成一个个母题,甚至丰富成一个个“时空体”,俄国最新一部《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德米特里•贝科夫(Дмитрий Быков)就归纳出帕斯捷尔纳克诗中的这样六个“时空体”,即“莫斯科”“佩列捷尔金诺”“南方”“高加索”“欧洲”和“乌拉尔”。
其次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亲近自然、感悟人生的主题内涵。1965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被列入著名的“诗人丛书”出版,该书序者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Андрей Синявский)在其长篇序言中写道:“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中的中心地位属于大自然。这些诗作的内容超出寻常的风景描绘。帕斯捷尔纳克在叙述春天和冬天、雨水和黎明的同时,也在叙述另一种自然,即生活本身和世界的存在,也在诉说他对生活的信仰,我们觉得,生活在他的诗中居于首要位置,并构成其诗歌的精神基础。在他的阐释中,生活成为某种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东西,是渗透一切的元素,是最为崇高的奇迹。”对自然的拥抱,对生活的参悟,的确是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中两个最突出的主题,而这两者的相互抱合,更是构成了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意义内核。在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中,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我”往往是隐在的,而大自然却时常扮演主角,成为主体,具有面容和性格,具有行动和感受的能力,诗中的山水因而也成为了“思想着的画面”;置身于大自然,诗人思考现实的生活、人的使命和世界的实质,试图在具体和普遍、偶然和必然、瞬间和永恒、生活和存在之间发现关联,这又使他的抒情诗成了真正的“哲学诗歌”。
最后是帕斯捷尔纳克诗歌创作的象征意义。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纵贯20世纪俄语诗歌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到20世纪下半期,他和阿赫玛托娃成为白银时代大诗人中仅有的两位依然留在苏联并坚持写诗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标志着一种强大的诗歌传统的延续,无论就创作时间之久、创作精力之强而言,还是就诗歌风格的独特和诗歌成就的卓著而言,帕斯捷尔纳克都是20世纪俄语诗歌中的佼佼者。帕斯捷尔纳克悲剧性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也折射出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乃至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命运,他在《日瓦戈医生》中展示出的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之命运,几乎就是他本人的一幅历史自画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自身也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文化价值,在几十年的创作历史中,无论社会风气和美学趣味如何变化,帕斯捷尔纳克始终忠于自我的感觉,忠于诗歌的价值,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又恰恰表现为对生活真理的忠诚,就总体而言,他的诗歌创作,就像曼德施塔姆对阿克梅主义所下的定义那样,也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