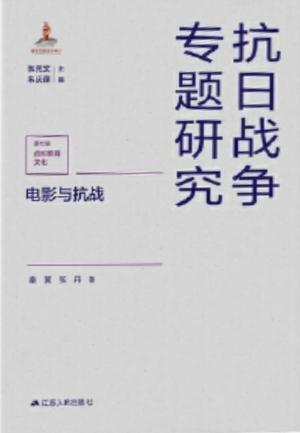 【书 名】电影与抗战
【书 名】电影与抗战
【作 者】秦翼,张丹 著
【出版者】江苏人民出版社
【索书号】K265.07/1230
【阅览室】花津校区社科阅览室二
作者简介
秦翼,女,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现为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民国电影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电影电视史。
张丹,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电影史研究专著,以十四年抗战期间电影的发展为整体考察对象,贯穿起局部抗战和全面抗战时期电影在民族危亡下的电影思想、技术、艺术革新、制作力量及政策的变化。从抗战前中国电影的民族化之路、战争形势下电影界的整体转变到抗战时期电影思想建设,从国统区包括故事片、纪录片、动画片在内的抗战电影宣传到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电影事业的建立与成长,从上海和香港两座“孤岛”的电影生产到沦陷地区受到的电影文化侵略,作者最终完成了对抗战时期电影文化的全面书写与评价。
三、找寻影业和影人的历史性连接
目前通过海量数字资源库,我们确实能够十分便利地利用关键词找寻到历史中的影片、影人的各种痕迹,这不仅直接推动了电影史实考证的众多突破,更进一步影响了近年来电影史的研究走向。但对历史细节的考证,对于电影史整体研究的最终意义何在?如何才能将数字化考据的零散成果拼贴成中国电影历史的整体版图? 就十四年抗战电影历史书写来说,其目的并非仅仅做一个拉长时限的抗战时期电影研究,而是努力找寻更具完整性的战争时段中前后电影产业发展的整体线索和作为电影创作主体的电影人之间的历史性连接。
战争是国家之间的极端政治状态,中国抗日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亚的主要战争,不仅是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漫长过程,更牵涉到长达十数年世界各国的利益争端。电影从诞生起就是包含着全球化动机的产业,中国在18世纪末就被动接受了电影,到19世纪初又主动发展起民族电影业。但由于技术、观念的落后,在电影生产上始终受到主要来自欧美的影响和制约。从现存报刊广告、放映资料、进出口贸易数据、公司经营报表及影人口述中我们能够发现,全面抗战前,欧美电影业在华收益十分可观,而日本胶片和影片却都受到抵制。侵略与抗争不仅体现在电影创作的审查与控制上,更体现在产业、经济手段的较量上,抗战时期则尤为显著。以早期中国电影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和香港为例,民营电影资本受到国际金融形势的严重影响,需要大量资金先期投入的电影业,在银根宽松与紧缩的经济条件下,境况迥异。战争的情势也大幅度影响了进口电影影片数量及设备、耗材的价格,对于屡陷困窘的国产电影业来说可谓雪上加霜。全面抗战时期,各国政治势力的博弈在产业布局上仍有体现。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地区掌握了电影制作放映的主导权,甚至在原本电影业并不发达的东北建立“满映”,大肆推进电影“国策”宣传。而在上海、香港两个“孤岛”,租界方面对于中日矛盾却采取极力回避的态度,虽然也曾迫于压力阻止辱华电影在上海公映,但更多时候是限制中国电影中表现抗日情节。这种软弱使租界沦陷后日军对上海电影民营业的全面控制显得毫无悬念。而大后方国民党官营电影则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从物料供应到人才交流,多位美国导演拍摄记录了战争中的日军侵略行径,留下珍贵的大后方影像材料。
战争造成的极端状况也引发了电影产业的局部小气候,最典型的就是上海“孤岛”。在日军围困、租界管制、国民政府暗中干预的种种限制下,在资金、物料都极度缺乏的状况下,“孤岛”上的民营电影公司却在不到四年中拍摄了两百余部影片,形成以往影史论述中所谓的“畸形”繁荣。深入考察该时期“孤岛”的作品,我们却能够发现其背后对故事类型、成本控制、明星形象、演员配置、观众心态乃至档期控制、舆论炒作等种种商业手段的熟练掌握。古装片、都市爱情片、侦探片、恐怖片、人物系列喜剧甚至科幻片、动画片……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中,类型的拓展从未如此丰富,类型化生产程度也从未如此之高,在此基础上的“繁荣”没有半点“畸形”。到沦陷时期,由于受到的政治制约更加严苛,电影创作者在任何故事中都糅进了已十分成熟的爱情伦理套路,是类型变异与融合的创作。
我们也能观察到战争威胁中作为早期电影业主体的民营电影公司经营者和创作者立场的变化。他们在战争一开始就有深入前线战场拍摄纪录片的热情,又积极接纳文学戏剧界的进步人士加入电影创作。但是面对国民党当局对电影业的拉拢控制,他们又显现出一定程度的积极配合,甚至在全面抗战前曾一度大拍“软性电影”。他们十分希望投入“国防电影”的摄制,但是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任何实质性帮助,因此局部抗战期间电影中呈现的抗争救国意识,是夹杂在各种商业、意识、娱乐的平衡中的。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官方电影公司出产的各类抗战故事片仅为40余部,纪录片也为数不多,电影的抵抗和宣传事实上仍主要来自民营电影公司,是一种影像的民间斗争。也因此,这种斗争不可能是强势的、鲜明的,它们可能是借古喻今、可能是微言大义,甚至可能是模棱两可的。而在沦陷地区,被溃败的国民政府抛弃的民营影业完全被日方吞并操控,这是民族电影业发展中应该被正视的最深沉的伤痛。
就电影创作主体而言,沦陷的东北、华北、华中和大后方的电影创作者同样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在电影生产基地上海,孤岛四年和沦陷四年中电影创作者面对强大的政治高压,基本未出产反动献媚的影片,较好地保存了电影队伍的实力,避免了电影业的毁灭性损失。他们也进而在作品中体现出苦闷彷徨,发展了传统伦理题材,形成含蓄悠远的电影艺术表现方式。而后方的电影创作者则屡败屡战,在生存危机下实践电影抗战宣传的各类形式,大大拓展了电影的表现疆域,极力促成民族意识觉醒和电影艺术革新。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影人和大后方影人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份标志,中国影人也由此产生分流,但电影人之间的艺术传承与精神连接是不会中断的。战后的中国电影呈现出与战前“青春中国”影像截然不同的气质,艺术家将战时与战后的自我感悟投射于银幕,使“中年”成为对民族灾难的痛切、对重拾旧梦的希望与失望、对自身命运嗟叹的一种重要表达。这种战争造成的民族影像风格转变,体现了中国电影创作主体的心路历程,是影人研究十分独特的样本。
抗战爆发后中国电影进入虽短暂但高度发展的艺术黄金期,由于缺乏对包括沦陷地区在内的战时电影艺术的充分研究,这样的高峰显得凭空而来。战后电影是战争期间各地区特色的融合和延续,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气质。而在一代代影人的影像书写中,抗战也一再被回溯,形成了另一种传承和连接。当前,我们已经有可能搁置政治争端和民族情感,客观地看待抗战时期的电影创作,作为广泛而持续的存在,它完全不应该成为电影历史中的一个“黑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