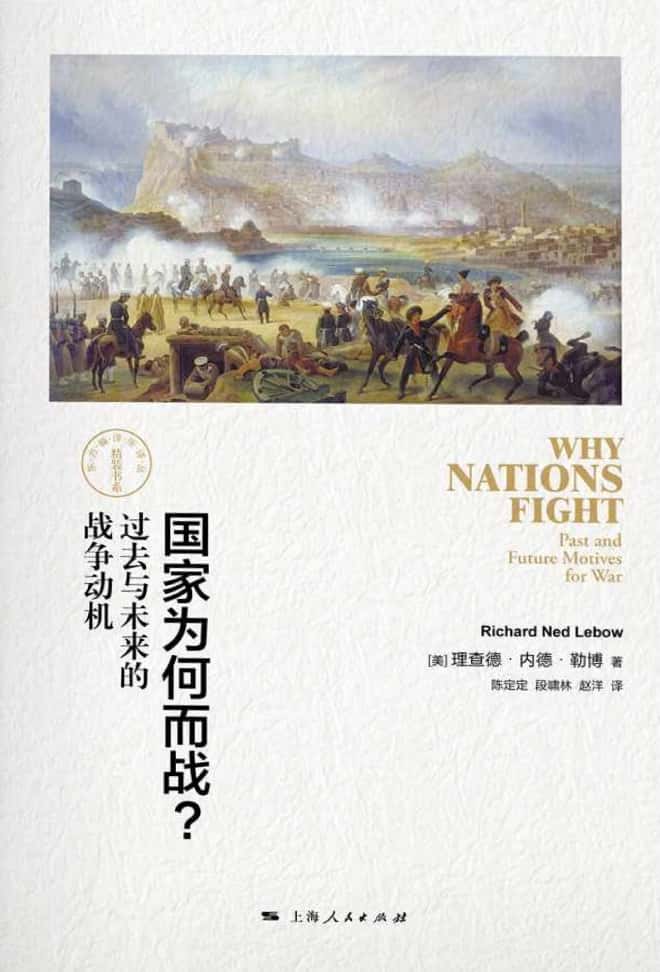
【书 名】国家为何而战? 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
【作 者】理查德·内德·勒博 著 陈定定,段啸林, 赵洋 译
【出版者】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索书号】D068/4443(2)
【阅览室】社科三阅览室
作者简介
理查德·内德·勒博
达特茅斯学院的詹姆斯·弗里德曼讲座教授,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世纪教授。
他有多部著作,其中《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获得了美国政治学会以杰维斯和施罗德命名的国际历史和政治学图书奖,并被英国国际关系学会授予苏珊·斯特兰奇年度图书奖,《政治的悲剧视角》(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获得2005年度亚历山大·乔治政治心理与国际社会图书奖。
内容简介
借助于原始数据集,本书作者考察了过去三个半世纪里战争的分布。和经典的认识不同,他指出,只有很少一部分战争是由安全或者物质利益所驱使的。相反,绝大多数战争是对于地位、复仇——试图击败以前侵占自己领土的敌国以洗去耻辱——的追求。勒博认为,今天,战争不再能够有效地服务于这些动机,其效能变得日益适得其反,而这一政治事实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有战争?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但却不那么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本书作者通过建立以个涵盖所有崛起国和大国的战争的数据库,对其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关于战争起源的六个假设,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基础上,把欲望、激情和恐惧看作外交政策的主要动机,其中,激情又被认为是近几个世纪以来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本书通过对数据集的研究,较为客观地考察了过去几个世纪的战争分布,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战争作更加详细和令人信服的预测。
中文版前言
我很高兴自己的著作和中国的读者见面。我的数据集和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欧洲的历史,因为直到19世纪末才产生了国际体系,但是我的观点对于历史上和现在的中国也同样适用。
简单地说,我在我上一本著作《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延伸出关于战争起源的六个假设,我建立了一个涵盖所有崛起国和大国的战争的数据库来检验这些假设。我的理论建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基础上,把欲望、激情和恐惧看作外交政策的主要动机。这三个动机中的两个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被广泛讨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植于欲望,而现实主义强调了恐惧。“thumos”翻译成英文是“spirit”,但这个翻译是个糟糕的翻译。激情产生了自尊,这是一种普遍欲望,它的实现需要赢得其他重要团体的认可。通过这些认可,我们才能自我感觉良好。实现自尊价值的驱动力十分强大,人和国家一样,往往会牺牲财富或者安全来追求实现自尊。荷马的《伊利亚特》是一个对以武士为基础的荣誉社会的有见地的描述,据此,我构建了一个建立在激情基础上的政治范式。它会导致国家间冲突,因为荣誉和地位的金字塔等级森严。不像财富,荣誉和地位是相关性的。正如托马斯·霍布斯所观察到的,如果所有人都得到荣誉,那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到了荣誉。
这三个动机对于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团体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国家不像个人,它没有感情,但是国家和国家的领导入代表他们的政治精英或公民而行动。人民有感情和需要,人民需要他们的领导人为他们提供安全;为他们增加财富创造条件。他们频繁地把实现自尊的需要提到国家层面,国家的成功让人民高兴,失败让人民感到耻辱。这在国家对荣誉和地位的追求中得以充分体现,国家总是渴望被认可为地区或者世界大国,成为除了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而被人仰慕的政治单位。荣誉是一种认可,这种认可通过国际体系内成员所普遍尊重的规则体系所确立,与广泛的国家间竞争所获取的地位密切相关。当规则体系被打破,荣誉让位于地位,国家和地区体系会变得更加暴力化。中国读者对于国家的自尊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会产生共鸣。
我的六个假设建立在对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对战争的解释的批判基础上:现实主义、权力转移理论、马克思主义、理性主义和定量分析。我的假设和这些理论或者路径的多数假设和预测相左。我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激情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地位、荣誉或者复仇的欲望(复仇也是激情的一种体现)合在一起,可以解释我的数据集中68%的战争。相反,恐惧(安全)和欲望(财富)分别解释了18%和8%的战争。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安全在国际事务中不重要,如果你是被攻击的国家,安全就是最重要的。
我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个假设:主导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并不会相互攻击对方,这和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完全相反。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因为美国的强硬派一直以权力转移理论作为基本框架来分析中国崛起对于大国权力格局的启示。他们认为,所有的崛起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追求重新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不惜发动战争,因此他们认为中美之间爆发冲突十分有可能,甚至不可避免。这一论断缺乏历史证据的支持。我的数据集表明,崛起大国和主导大国都倾向于攻击弱小的第三国和正在衰落中的大国。这对于试图获取霸权的主导大国和寻求大国地位的崛起国家而言,是一个理性的策略。
理性主义者和现实主义均势主义者认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基本上是由于权力失衡,或者国家受到不完整信息的影响而错误地估计权力均势而引发的,尤其是那些大国被牵涉其中的战争。我的数据和以前发表的一系列案例分析挑战了这些观点。误判有很多,但并不是由于缺乏信息所引起的。更多情况下,这是因为领导人在诉诸武力之前不能够认真进行战争成本的权衡。一个引入注目的事实是:自1648年以来,大国和崛起国家输掉了一半以上它们所发动的战争。我建立了一个涵盖1945年以来所有战争的数据集,包括一些次要的战争(指没有大国参与的战争),数据表明,三分之二的战争发动者输掉了它们所发动的战争。如果战争发动者进行了任何理性的战争成本估量,并且只在它们认为自己能够赢得战争的时候才发动战争,它们赢得自己发动战争的比率要远远超过50%。1945年以来的战争发动者只赢得了少于三分之一的战争,为了解释这一事实,我们必须考虑心理学上的解释,这正是我在本书里面所做的。
最后,有很多战争爆发的起源是复仇,以重新夺取在前面战争中丧失的领土。这些战争的发动者基本都是衰落的大国和弱小国家,并且它们基本上都输掉了这些战争。复仇是个很重要但非理性的动机。
数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动机的分布并不稳定,这表明,战争和动机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存在着不吻合。第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和欲望有关。在大国和崛起国家发动的所有战争中,经济收益是18世纪战争的一个重要动机。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开始逐渐否定财富有限的观点,主张财富可以通过劳动分工、工业化、规模经济和国际贸易与合作来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使各国逐渐意识到:和平有助于增加财富,战争则会损害经济发展。
第二个历史性的变化是西方对于安全的重新诠释。集体安全要比“自助行为”能够更好地实现安全利益。实现集体安全的努力始于维也纳会议和凡尔赛会议,这并没有成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集体安全的努力硕果累累。正如卡尔·多伊奇所希望的那样,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共同体内成员之间的战争变得不可能。
导致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第三波学习的浪潮,我的这本书正试图定义和推广这一学习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关注了激情以及地位在国际体系中的逐渐变化。国际关系发端于欧洲,大国间关系说明了贵族式的武士社会的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中,地位只有通过战争的胜利来获得。近代以来,每一个崛起国家都要赢得一系列战争才会被大国俱乐部承认为“大国”。
以地位为基础的战争首先被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和美国,以及随后的苏联所挑战。这三个强国通过它们的军事成就获得大国地位。今天,欧盟、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加拿大、巴西、日本和中国等大国之间存在一个范围更广的,更加成功的竞争,它们看重荣誉胜过地位,并且希望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荣誉。这种竞争最为常见的基础是民主政府、公平地对待少数群体和财富。在财富这一点上,国家倾向于在使本国国民受益的同时。也能够给欠发达国家带来利益。通过参加类似维和的国际活动来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也成为国家获得荣誉的重要方式。相反,使用武力逐渐变得会损害国家的荣誉和地位,除非获得了联合国或者适当的地区组织的授权。这一点在美国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得以体现,民意调查显示,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尊重在伊拉克叛乱之前就直线下降。二十年后再回首,我们会发现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拐点。
中国读者应该会从这些发现中受到鼓舞。国家间的战争在减少,因为诱发战争的主要动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并且通过其他非战争的活动表现出来。中国已经通过和平方式成功获得了荣誉和地位。中国被认可为一个大国表明,没必要通过发动并赢得战争来获得这种地位。在未来,中国可以通过遵守、促进和改革,而非挑战现有的国际规范获得更多。
并非所有人都认同我这个“未来战争会减少”的预测。但是我认为,对我的批判需要读者基于清晰的理论假设和正确使用现有数据来做出判断。毕竟,类似的争论和相互学习的过程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