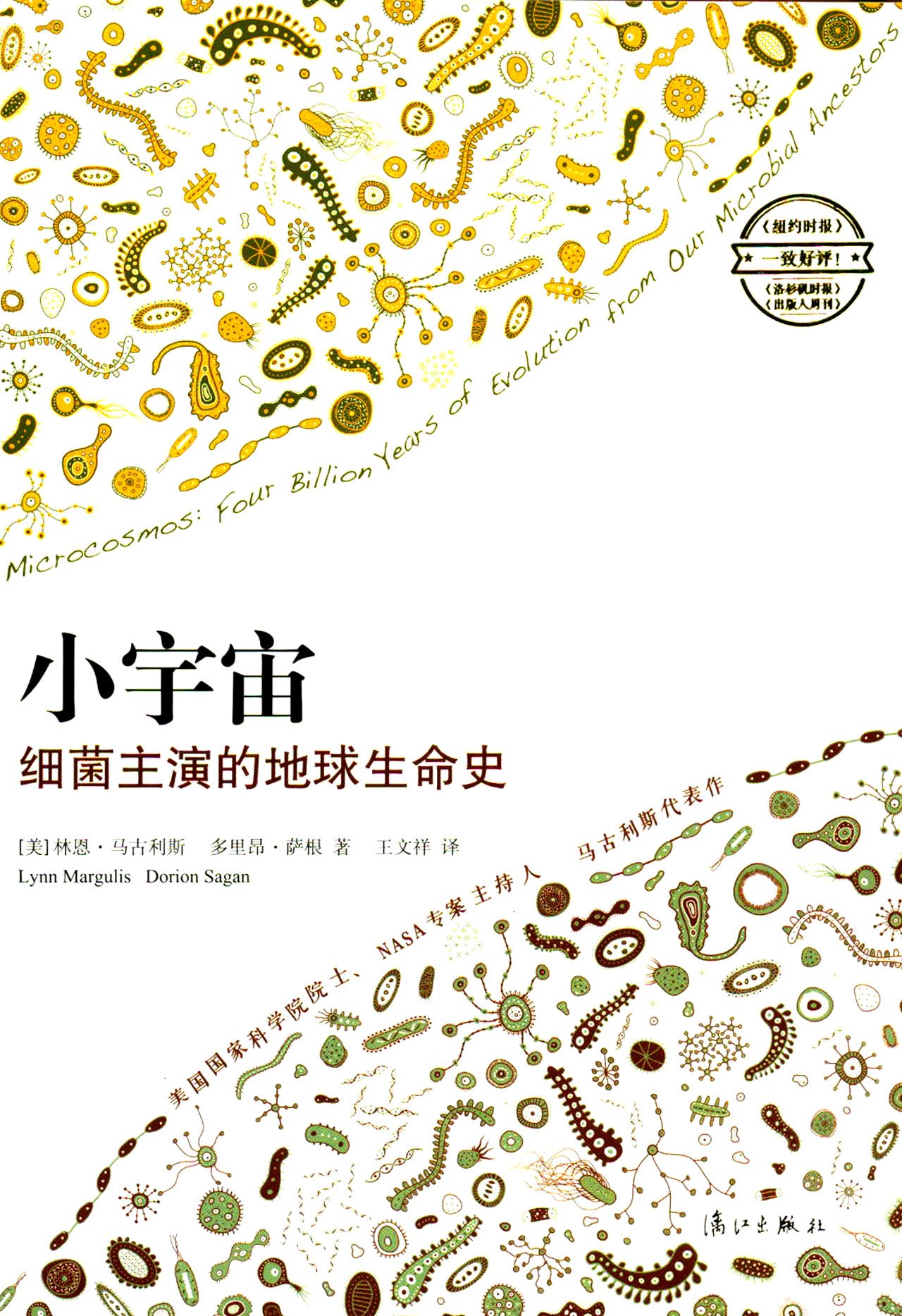
【书 名】小宇宙:细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
【作 者】(美)林恩·马古利斯,(美)多里昂·萨根 著 王文祥 译
【出版者】漓江出版社
【索书号】Q11/7742
【阅览室】社科二阅览室
作者简介
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1938—2011),出生于芝加哥,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学博士,曾任波士顿大学生物学教授,现任马萨诸塞大学荣誉教授、美国航空航天总署行星生物计划共同主持人。她以研究真核生物的进化备受推崇,是现今生物学界普遍接受的“内共生学说”的主要建构者,此学说解释了细胞中某些胞器,如线粒体的由来。马古利斯发表过上百篇学术论文,出版著作十余本,曾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与俄罗斯科学院,并在2000年获颁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多里昂·萨根(Dorion Sagan),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与马古利斯之子,美国著名科普作家,出版著作20余部。他擅长以优美的文笔描摹科学理论与观点,写作主题围绕着生物学、科学哲学与人类文化,作品被译为13种语言。萨根与纽约大学生物系教授沃克(Tyler Volk)的合著《死亡与性》(Death and Sex)获2010年纽约书展非虚构类冠军。
王文祥,台湾大学地质学研究所博士,地质工作者,专长为火山定年、砾石层剪力强度及边坡稳定度。著有《阳明山火山的故事》等。
内容简介
提到“进化”,你的脑中是否浮现出猿猴转变成人,或是鱼长出脚爬上陆地的画面?其实,我们都看错了演化舞台上的主角。细菌,才是主宰地球生命进化的关键。
林恩·马古利斯、多里昂·萨根在这本《小宇宙(细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中,将前所未有的演化思维呈现在我们面前:动植物细胞中的线粒体和叶绿体,竟然曾经是独立生存的细菌?单细胞生物间互相捕食的过程,也许是多细胞结构的起源,甚至形成了复杂的动物,例如人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本书是回顾生命进化的时光机,带领我们回到创世之初,看充满岩浆的炙热的不毛大地,如何冷却成浩瀚的原始海洋;而最早的无生命物质,又如何生成有秩序的生命结构?《小宇宙:细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让我们看见细菌如何引领地球的生命,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微生物到我们。
我们是怎样的一种生灵?从细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我们会得到新的答案。
林恩·马古利斯、多里昂·萨根著的《小宇宙(细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不仅首次从细菌的角度描绘了波澜壮阔的进化历程,更以丰富的例证与有力的说明,继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进一步将自诩为万物主宰的人类拉下了进化的神坛。
以为凭借高度的智能与堪比造物主的创造能力称霸了地球的人类,或许不过是小小细菌的殖民地。本书通过对生物进化史的全新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人类在进化历程中地位的新视角。
这本书的内容是介绍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存在过去的难以计数的生命与现存生物之间的复杂关联性。马古利斯及萨根提出了不同于我们过去数十年接受的新世界观。
——刘易斯·托玛斯(Dr.Lewis Thomas,本书序言作者)
《小宇宙:细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具有明白易懂的散文风格。叙事清晰,又能使读者的想象力奔驰;最大的优点,是书中充满科学事实,而不光只有抽象概念或见解。这本书超越了科普作品及科学报道的疆界,开创了新路。
——《纽约时报书评》
引人人胜、欲罢不能,极其杰出的科普作品。《小宇宙:细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浅显易懂地解释了久远的进化史和近年发现的科学证据。
——《洛杉矶时报》
本书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编年史,它提醒我们,生命欣欣向荣的源头,在于我们肉眼难见的微生物小世界;而微生物,也赋予了我们跨出地球、跃向“超宇宙”的可能性。
——《出版人周刊》
《小宇宙:细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属于那种极少数能够为读者带来永久性改观的作品。自然界永远在变化,即使它的很大一部分还隐而不显。本书以严谨、清晰而极少掺杂行话的风格写就。
——克里斯平·蒂克尔(Sir Crispin Tickell,牛津大学格林学院)
这是一本人人都适合阅读的书。虽然这部迷人作品中丰富而激动人心的观点来自于新近的科学研究,却能让只懂一点儿生物学的人轻松掌握。……《小宇宙:细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包含了诸多信息与有趣细节,而这些都展现出各种生命形式之间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彼得·班亚德(Peter Bunyard,《生态学家》期刊)
序言
一部精彩绝伦的星球生命传奇
刘易斯·托玛斯
对读者来说,前言的功用有时是对一本书的评论,或者是预先提示他们书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阅读这本书时,除非读者对近代微生物学、古生物学以及进化生物学领域一直有所接触,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有一连串的惊奇,甚至震撼。
人定胜天?
这本书的内容是介绍有关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存在过去的难以计数的生命与现存生物之间复杂的关联性。马古利斯及萨根提出了不同于我们过去数十年接受的新世界观。这个新观点是以全球各实验室实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经过整合及串连之后所导出的结论:自然界本身完整而不可分割;生物圈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巨大、完整的生命系统。
记得很久以前,我曾出席一所大学名为“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之系列专题讨论。其中大部分提及了人类如何能对自然界整顿、修理一番,从而让世界上的事物依照我们的理想运作;如何榨取更多的地球资源;如何保存某些荒野地区以供我们游憩;如何避免污染水系:如何控制人口等。事实上,它整体的观点是:自然是遗留给人类的财产,是人类所拥有且能够支配的综合公园、动物园及自家的果菜园。
这些观点就是我们传统的想法。可是您一定不满足,想再深究下去。毫无疑问,人类在占领地球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以强势物种的外貌主宰地球。也许在人类形成初始,刚从树上跃下来时,还是脆弱、可能犯错的动物,除了拇指能和其他四指对合以及夸张的大脑额叶之外,实在没有什么足以夸耀的东西,顶多能藏身洞穴中研究如何取火。
但我们终究接管了地球。现在的我们似乎无所不在,操纵着每件事物。从北极到南极、从山巅到深海,甚至登陆月球,放眼太阳系。我们永远都是地球的主宰、进化的顶点、生物成就的极致。
其实,如果你抱持着漫不经心的态度,这的确是看待这个世界的简单方式。
我们还年轻
然而,我们还有另一种看待自己的角度——这本书正是这种观点的指引。
以进化的历史来看,我们在地球上才刚刚出现不久,也许仍有其他比我们更年轻的物种,但他们散播的范围,尚赶不上我们所达到的程度。让我们确实认为人类出现的铁证,诸如语言、歌唱、工具制作、生火取暖的能力以及喜欢安逸及好战的人性,一共只能追溯数千年而已;再往前看,人类历史无异于其他动物的历史。以物种的观点而言,我们还年轻,也许才刚开始发展,仍处于学习成为“人”的阶段。我们是未成熟的物种,仍然容易受伤、出错,甚至还冒着核战后,徒留薄薄一层放射性化石的风险。
弄清楚自己在进化谱系中的位置,有助于改变我们的观点。过去我们曾认为人类由上帝所创,于宇宙形成之初,就已占有一席之地,准备好要成为其他动物的主宰,虽然连衣服都还没穿上,却已经热心为其他动物命名了。然而,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我们却必须面临“大猿是我们进化家谱的一部分。黑猩猩是我们的表亲”的窘境。
许多孩子在青春期,都同样会经历一段痛苦的日子。他们总不满意父母,希望自己的父母与众不同,最好像对街某家父母一样。其实,祖先是外表古怪的原始人,并不是真的那么可耻。但如果可以重新选择的话,大部分人仍情愿自己拥有王公贵族的血统,而且最好就此为止,不必再追本溯源了。
“它”是我们的祖先
现在看看,是什么让我们左右为难。我们在进化上的起点,是大约三十五亿年前的细菌,所有生命最古老的祖先。地球上所有的事物都得回溯到“它”。
尤有甚者,尽管我们大脑额叶发达,辩才无碍,具有音乐涵养,俨然优雅大方,但这些微生物老祖先始终与我们同在,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它们的一部分。
一旦我们勇敢面对这个事实,将惊叹它是一个伟大的故事,一首波澜壮阔、不可思议的史诗,一部精彩绝伦的星球生命传奇。但请注意,故事还没结束……
马古利斯花了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研究这个故事,她本身的研究成果更为这个故事加入许多重要的细节。现在,她和萨根以文学的形式。把这些成果一起放在这本非凡的书中,使它完全不同于我过去读过的有关进化的一般书籍。
生物进化史中绵延最久的事迹,是引人人胜的题材:二十五亿年的漫漫岁月,我们的微生物祖先发现了一条共存共荣的生存规则。这也正是人类必须研究的习性,探求使我们继续生存的线索。
大部分流行的进化题材及问题,都只从数亿年前开始讲起。对于最早的多细胞生物形式大多只略为提一提,然后就快速转移到脊椎动物的蓬勃发展。好像“原始的”“简单的”细胞在地球漫长的进化时间里什么事都没做,只等待着其他生物形式的好戏开演。马古利斯及萨根修正了一般人对真实生命的误解。他们揭露出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每项生存技能,其实最古老的细菌早就已经知道了。
教我们要谦逊
或许我们早已预知自己的真正起源。从隐藏在“语言化石”中、关于“人类”这个字的古老字根,可以一窥究竟。数千年前的初期印欧语系(没有人确知其年代)将地球拼成dhghem。这个词意味着由泥土(earth)变成沃土(humus),代表着我们是土壤细菌的杰作。同时,它也教导我们谦逊(humble)、人性(human)及人道(humane)。
在这里我只是概略地提一提。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深意,则在本书有详细的阐述。
(本文作者托玛斯Lewis Thomas,曾任史隆凯特林癌症纪念研究中心Memorial Sloan-Keaering Cancer Center名誉理事长)
文摘
原始地球
那时,约46亿年前,有几个条件使得地球处于适合生命产生的状态。首先,它很接近能量来源——太阳。第二,在绕行太阳的主要行星中,地球还不至于太靠近太阳,以致让元素都汽化成气体或是熔化成熔岩:同时它的距离也没有远到会让气体凝结成冰、氨及甲烷,如同土星的最大卫星土卫六那样。此外,与太阳的距离也使得水在地球上呈液态,但在水星上却蒸发到太空中,而在木星上则都凝聚成冰。最后一个条件是:地球的大小适中,足以将大气层留住,使元素可以流动循环,但也不会大到让重力把大气层都凝集在一起,让太阳光线无法透过。
太阳燃烧初期,爆炸性的辐射风暴横扫刚成形的太阳系,搅动了地球及其他内行星的早期大气层结构。氢气太轻,很难让地球重力保留下来,因此它们不是飞到太空中,便是和其他元素结合,产生形成生命所必须的重要组成。那些能留下来的氢气,有些和碳结合成甲烷(CH4),有些和氧结合成水(H2O),另外有些和氮结合成氨(H3N),而有些则和硫结合成硫化氢(H2S)。
这些气体。再经重新排列组合成长链状化合物之后,便构成我们身体里实际的基本组成。但是,在木星、土星、天王星及海王星等巨大的外行星上,直到现在它们仍然以气体的形式保留于大气层,或是凝聚成固体存在于行星表面的冰层中。
然而,在体积较小、较年轻、且表面仍呈熔融状态的地球上,比重力还复杂的其他现象,则开始将这些气体加入物质循环,以维持今天这个生机勃勃的局面。
炼狱大地
早期地球形成时的猛烈大气及高温,使得地球在冥古代(45亿至39亿年前,请参阅表一)的岁月里,没有坚硬的地壳,也没有海洋及湖泊,甚至可能连冬天的雪及冰雹都没有。整个地球是一个熔融的熔岩火球。地核放射性元素铀、钍及钾衰变所产生的热,使整个地球都燃烧起来。地球的水以蒸气喷泉方式自内部喷射出来,由于温度太高,它们从未变成雨滴降到地面,只是成为未凝结的水蒸气飘浮在大气中。大气层很厚,而且充斥着毒性极高的氰化物及甲醛。这时的大气既没有可供呼吸的氧气,当然更没有任何利用氧气的生物产生。
地球上没有任何岩石可以逃过这个地狱般的原始混沌状态。冥古代的定年,是由陨石以及阿波罗号航天员带回的月球岩石所测定的。当较小的月球在46亿年前开始冷却时。地球仍处于熔融状态。大约直到39亿年以前,地球表面才冷却到足以形成一层薄薄的地壳,不平稳地盖在底下仍是熔融的地函上。此时的地壳常遭到底下的熔岩穿凿,或是陨石自空中撞击出大大小小的坑洞。火山自裂缝及罅隙喷发出来,溅洒出熔融的硅化物。陨石则从天而降,剧烈撞击地球,它们有些大得像山,而且比美、俄两个超级强国的核弹头更具爆炸威力。这些陨石带来大量太空物质,在混沌大地上撞出一个个坑洞,抛射出巨大尘粒云柱。乌黑的尘云遭猛烈的巨风吹扫出来,绕着地球打转数个月,直到最后整个沉降到地表上。此时,尘云惊人的摩擦作用,造成广泛分布的雷鸣及闪电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