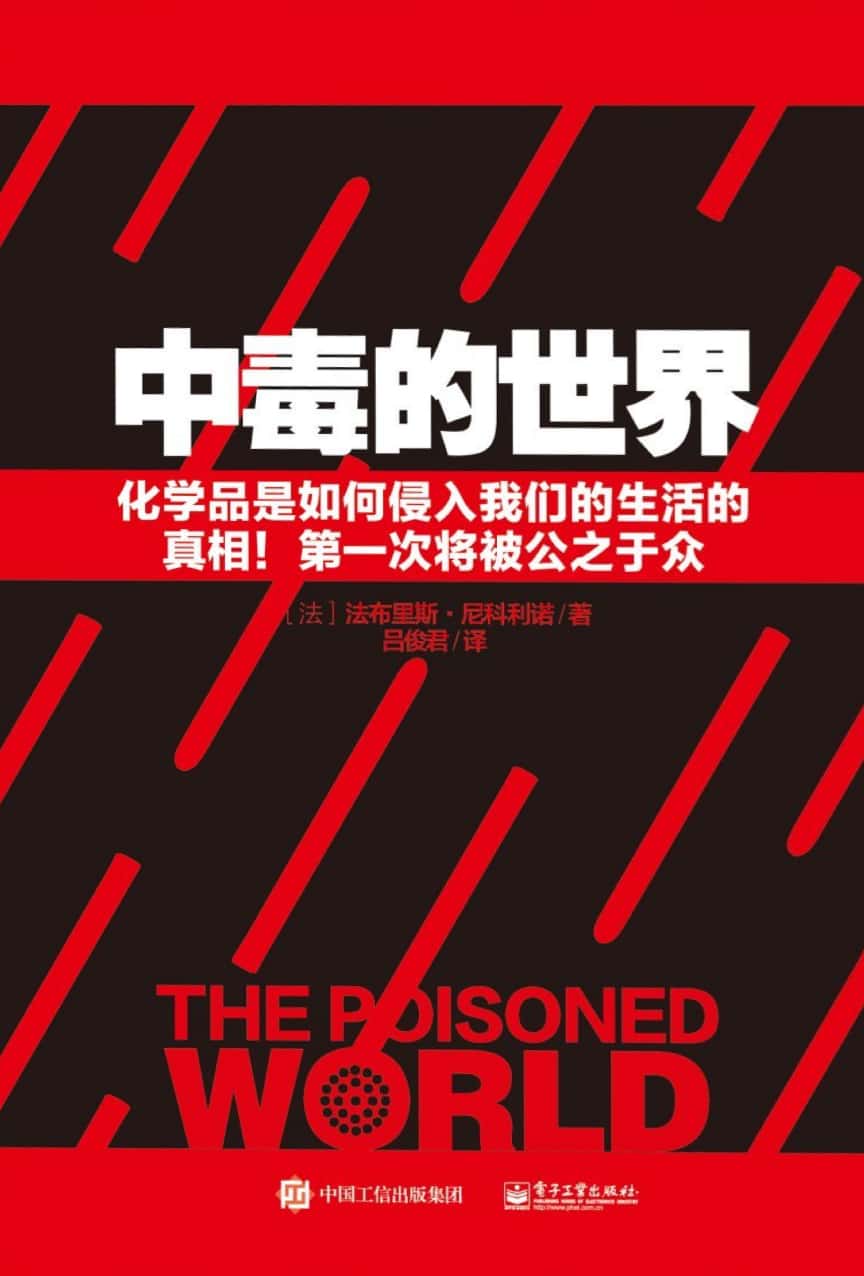
【书 名】中毒的世界
【作 者】(法)法布里斯·尼科利诺 著 吕俊君 译
【出版者】电子工业出版社
【索书号】TQ086.5/7722
【阅览室】自然阅览室
作者简介
法布里斯·尼科利诺
记者,法国《十字架报》专栏作者,曾出版《谁杀了环保?》《一滴水的旅程》《肉工业威胁世界》等书。
《中毒的世界》一经推出,立刻在法国等欧洲国家引起强烈方向,短短一个月,销量逾万。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前所未有的书,它一次完整地剖析了生活中化学品肆虐的可怕局面。全书以犀利不乏幽默的笔锋,以及揭露一切真相的态度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七亿不同的化学分子会出现在水里、空气里、土地里、食物里,甚至是新生儿的血液里;拜尔、巴斯夫等化工巨头是如何发迹的;为何在同一时间,癌症、肥胖症、厌食症、阿兹海默症、帕金森症、哮喘与自闭症突然泛滥;所谓的饮用水里到底藏着什么;跨国企业如何用包装过的信息欺骗全世界……
作者是法国《十字架报》、《查理周刊》专栏报记者,在2015年1月7日袭击事件中幸存但多处受伤。正如作者所说“也许真相可怕,但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有知道的权利。”
本书分为五部分,按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轴讲述了化学品的产生,被战争年代参战各国的利用,现代化学工业对环境对人类的进一步影响和毒害,官方组织对一切真相的隐瞒与无力控制,以及化学品对人类未来的致命性打击。化学品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一边在享受它带来的福泽,一边在无知且无助地被它推向可怕的深渊。
序言
在这个梦幻的世界里,一切似乎都有可能。冲突是礼仪的主宰之一,最强烈的激情滋养着冲突。人们疯狂地相爱,不顾一切地投入一个一毫秒前还不认识的人的怀抱。人们憎恨了,就以音速逃跑,不扭头去看那不曾存在过的过往。构成天地万物的是闪光片、调色板、颜色、形状和不断的相遇。
这个宇宙终究是临时性的。在这临时的宇宙里,运动是持续的,冒险是持久的,不可思议之事是真实不虚的。未持护照便进入这个未知的广阔国度里的你呀,忘掉你的畏惧,把可怜的临终圣餐留在门口吧,它们只会把你塞满罢了。化学是一个奇迹,我们应该惊讶地欣赏它,至少在一开始时应该像一个发现幸福的孩子一样。
话说回来,那物质又是什么呢?我们甚或可以问,就我们的感知而言,物质存在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一滴水,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它,但它却隐瞒了50万亿亿个原子。方便起见,我们就说这些原子的尺寸太小,是不可感知的。当然了,是不可被我们感知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回想起《微观世界》的效应。1996年,导演克劳德·纽利迪萨尼和玛丽·佩莱诺发现了“草中的族群”。他们在阿韦龙省的某一处田野里——别管是现实中的哪个地方了——采用适合昆虫和蛛形纲动物尺寸的透镜和仪器,展示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这里上演着无尽的诞生、战斗和相爱。
当然了,原子的生命似乎比红蚂蚁和独角仙的生命简单,但它囊括了后者并广泛存在于银河系。我们隔着这么远的距离看,银河系似乎是一个整体,但它其实是由无数个点构成的。根据美国开普勒天文望远镜的观测结果,银河系中至少有170亿个与我们的古老的地球大小相仿的行星。
一片嘴唇或者一只脚,希特勒或者甘地时间,在这种条件下也呈现出奇幻的轮廓。如果我们想完全像在我们所熟悉的维度里这样在其他维度里行动,我们就必须有天使一样的耐心。人们据此计算过,要想往天平的托盘上放入仅仅1克的硫,你就必须拥有6万亿个世纪,你得一个接一个地抓住硫原子,当然还是中途不能停歇的。
整个宇宙无非由一百来种基本的化学元素构成:据统计有118种,其中94种为自然元素。这些自然元素的化合就能解释存在的万物,无论是大棕熊还是一幅梵高的画作,是用餐围兜还是柳珊瑚,是三层厚的床垫还是一滴石油,是一片嘴唇还是一只脚,是希特勒还是甘地。从根本上说生命只是若干基本元素(比如氢、碳、氮、氧,还有铅、氯、钙、钨、碘等)的混合物。
那我们为其存在与否的问题争论了那么多个世纪的原子呢?英国的天才化学家约翰·道尔顿1803年就第一个提出了他的“原子理论”,他断言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而原子与原子在芭蕾舞一样的无休止的变动中互相结合。今天我们知道,原子包括一个由质子(通常)加中子构成的原子核,单这一个核就集中了原子的99.9%的质量;而原子核的四周围绕着比它大几万倍的电子云。顺便说一句:电子云的巨大表面积说明了物质的主要成分是“空”,就连混凝土也是如此。电子云,顾名思义,含有大量的电子。电子做超高速运动,但其轨迹始终不脱离其原子核外的一块区域,我们可以称之为“虚拟轨道”。
南美蟒蛇现身法式火焰薄饼中原子几乎从不孤立存在,它们通常聚集在一种叫做分子的结构中。把水晶和聚合体的问题放到一边。如果说原子是字母,那分子就是句子。原子仿佛永不停歇地在寻找一次运动、一次相遇、一次放纵。再以水为例来说吧。按照其分子结构,水质量的89%是氧,11%是氢。水是怎么形成的呢?每个水分子都是三个闲逛的原子结合的产物: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我们用化学式H2O来描述水,意思就是两个氢(H2)配一个氧(O)。再添上一个氧原子就变成了H2O2,也就是双氧水。分子就这样聚合原子,可以多达几千个,理论上原子的数量甚至可以是无限多的。在这一阶段,人们仍然不知道其间的引力是怎么产生的,更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
我们先要明确一点,那就是原子从来只是更换居住条件,或者说只是在各个种类的、无限多的制服之间更换。一个500年前曾参与过构成一条潘塔纳尔湿地蟒蛇的原子完全有可能会出现在2014年巴黎街头某人正在品尝的一张法式火焰薄饼中。
这种奇特现象的关键叫作“反应”,一种基于静电能的不可抗拒的吸引现象。分属于两个不同原子的电子——姑且称之为“单身者”好了——寻偶。他们以电偶极子的身份互相靠近,各自的一部分电子云相融合——各自的电子从而也融合在一起。这是一切反应的开始,哪怕它比这个要繁复纠结一千(或十亿)倍。
物质,不论其形状或来源为何,其表象总是气态、液态或固态的。但这句话的关键词是“表象”,以为其实有相反相对的力量在不断地互相中和,这才将元素排列得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起见,我们只取温度这一个参量。温度可以来一通大洗牌,将冰化成水,又将水化成汽,这种过程能改变一切。在固态下,分子几乎不能动,一个挨一个紧紧地挤在一起,很难按照某个稳定的方位游动;而在液态下,分子可以和邻居换位子,也可以自己转身。
每秒钟100亿次碰撞它们的结构可以概括,但它们的运动是变化多端的。物质成为气态时分子才算抵达自由之巅。O2分子(两个氧原子)在常温常压下以1500km/h的高速奔跑,而且每个分子每秒钟都会承受100亿次碰撞。
气态的分子简直是进入了急速的、广袤的天堂。这许多的碰撞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化学反应,从而引起分子结构的重组。我们不妨将事情简化,假定一个气态的分子A2由两个A原子构成,在气体的躁动中,它遇到了同样是气态的B2分子,那就可能催生出两个新的AB分子。然而这只是假定,因为或许无数每秒百亿次碰撞之中什么反应都没有发生。
这种运动和结果都是难以估量的、偶然的,且原子的重组只持续亿分之一秒。秩序纯粹是绝对无序的暂时平复。无序是本源。无序是基质。奥秘在火柴头上我们需要动用我们的贫薄的想象力才能描绘过去的人们在见证或者参与那些化学反应时多么心旷神驰。不得不从火种说起。是什么魔法点燃了火?我们的古人一无所知,我们可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燃烧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以壁炉里的火为例,首先要有燃料,即木头;其次是火焰的温度,它带来催化的能量;最后是任何燃烧都必不可少的助燃物,在我们的例子里助燃物是我们称为氧气的O2。
全部的过程无非化学反应,其中包括最开始的那个火花。火柴头上有一层磷脂覆盖着一层硫。磷在50℃就能燃烧,而后硫接力,直到火焰攻克了小木棍的头部。还需要一个刮板,通过摩擦给磷加热。当代的火柴头混合了玻璃粉和红磷。在遥远的过去,人们唯有拿两块木头互相抵住摩擦,直到引动燃烧那一程序。
那我们在炉膛前怀着那么多喜悦观赏的火光又是怎么回事呢?它一部分来自化学反应过程中的电子交换,一部分来自物体被加热到很高的温度时放射出来的光。木头含有——只是大约值,因为树种不同比例也不同——50%的碳、44%的氧和6%的氢。从碳到灰的剧烈转化理所当然地会带来原子与分子的重新分配。碳变成了二氧化碳,到了空气中,在若干步骤之后又将被正在形成中的木头吸取。二氧化碳从壁炉的排烟管散出后到别处,可能是很远的别处,去体验新的化学探险。在此我们只提及而不强调一点,那就是并非所有的碳最终都会成为二氧化碳。例如,一次不良的燃烧会附带产生一氧化碳甚至富含碳的炭黑。旧石器时代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人类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力去看待这些神秘的现象。幸好我们有了化学。捍卫好奇心您即将阅读的这本书绝对不抹杀好奇心。抹杀人类的好奇心就相当于控诉人类本身。人类过去、现在、未来都曾经、正在、必将探问其周围的无穷无尽的谜。化学正是探问之一。原子,并不像很多人相信的那样是宇宙的基本粒子,因为如上所述,它含有质子、中子和电子。但是我们从1964年——仅仅!——开始知道前两者也不是最基本的,因为他们由夸克构成,而夸克才算是“真正”的基本粒子,也就是不含有他物的粒子。
这一发现似乎给了那些当初自以为发现了第一要素的人当头一棒,而且似乎人类可以毫不费力地靠近炼金术士的“贤者之石”了。
这当头一棒,美国人默里·盖尔曼——夸克之父,1969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也没躲过去。因为“夸克”一词是从詹姆斯·乔伊斯的几乎不可迻译的《芬灵根的守灵夜》中窃来的。原词所在的那句话是:“Three Quarks for Muster Mark !”这是海鸟鸣出的几个词儿,我们勉强可以译作“三个夸克给穆思特马克!”这么说来夸克是一句戏言。
但盖尔曼的贡献不止于此。1954年,他引进了一个新的量子数,他命名为奇异数。在这种情形下,这个与新粒子的发现有关的词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一个常见的词,指涉的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说不尽的不可理喻。
光荣归于贾比尔·伊本·哈扬远古之人对化学知识的探索是一种优美的才智之举。人类中的少数个体能在蒸馏瓶和方程式中度过一生,只有极端凉薄之人才会不欣赏这种本领吧!隔了时空的距离看过去,波斯人贾比尔·伊本·哈扬——很有可能是他——在公元8世纪发现盐酸的举动充满了孩子气的喜悦,另一个波斯人阿布·巴克尔·穆罕默德·伊本·扎卡里亚·阿拉齐,在公元9到10世纪之间分离出硫酸和乙醚之举亦然。同样的还有大约五百年前的帕拉塞勒斯,他通过将硫酸倒到铁器上,第一次描述了氢气的形成。十七世纪初的迈克尔·森迪沃奇,他嗅到了氧气的端倪。随后的约瑟夫·布莱克,他的“固定气体”(也可以叫作“二氧化碳”)。还有拉瓦锡、伏特、盖-吕萨克、贝采里乌斯、法拉第,以及其他上百位化学家都是如此。不,这本书绝不是要给化学判罪,而是要通过大量难以辩驳的实例来证明:从化学探索中滋生的化学工业引发了一场针对所有生命体的不宣之战。这与做出发现的天才们无关,问题在于我们人类的无法逾越的局限性。
